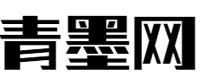就像一个狂欢节
“Gentlemen。”一个黑人环视了一眼办公室。
时间是7月13日,这里是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距离北京一万公里。
“我担心如果我们只请一位大酋长,其他酋长会觉得受到轻视。”
说话的是Royd,赞比亚卫生部的项目官,他戴着一副眼镜,在赞比亚,你很少能见到戴眼镜的人。Royd熟悉和酋长们打交道的方式,赞比亚一共有73个部族,每个部族都有一个大酋长,要在酋长的领地举办活动,即使是中央政府的活动,也必须显示对他们的尊重――去酋长的宫殿拜访他们,送上礼物,获得他们的同意。
特别是,如果你的活动是在酋长的领地上,劝说酋长的子民直挺挺躺好,挨上一刀,割掉包皮――这就是活动的全部内容,割掉成千上万赞比亚男人的包皮。
有一次为了让一位酋长同意这样的操作,Royd代表卫生部送了他一把猎枪。
“活动在Chipata?”又有人问。
“Yes.”Royd点了点头。他理解问话人语气里的潜台词,Chipata是赞比亚东部省的省会,东部省的男人们对自己的包皮有着强烈的执念,除了恐惧切肤之痛,也担心被人利用。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首都来的人劝你割掉包皮,然后那一小块血淋淋的皮肤,被送到邻境的莫桑比克,在那里,人们用成箱成箱的包皮换汽车。至于莫桑比克人为什么乐于用汽车换走他们的包皮,大概是巫师要做黑魔法。
在东部省,卫生部只好同意那些割掉包皮的人带走自己被割下的包皮,至于要拿那带血的皮肤怎么办,真是天晓得。
即使作出了这样的让步,在另一位大酋长领地,前年他们也只割掉了617块包皮,相当于酋长3万男性子民的2%。
如今他们要迎难而上。活动那天,他们要把一个知名歌手和他的乐队拉去Chipata,还要找一个戏剧团表演drama show,当然还有绕城游行,从中央医院去到小学,再绕道中学,男学生们都是他们的目标。志愿者将边走边拉横幅,上面是欢快的震惊体,“你还没有割掉你的包皮?!!”――整个活动就像一个狂欢节。
中国人大概会感到陌生,但包皮切割是人类最古老的外科手术之一,全世界有30%的男性割掉了包皮,在中国,这一比例还不到3%。
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了一项临床研究结果――切除包皮可以预防艾滋病,将通过异性性行为传播的艾滋病毒感染风险降低60%――这被誉为2007年十大科学发现之一。一项由WHO倡导的大型跨国运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展开,在14个平均艾滋病感染率超过15%、同时没有割包皮传统的非洲国家,推进全民的割包皮运动,让这些国家的男性公民,包皮环切率超过80%。不仅要割掉成人的,还有刚出生的男婴――割下2000万张包皮,就是这项运动的目标。
如果成功,将减少340万新的感染者。
割掉包皮,成了人类抗艾战争中的关键一步。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艾滋病毒新发感染总数的三分之二。赞比亚就有120万感染者,超过总人口的10%。这里还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地方,在赞比亚,到了2012年,男性的预期寿命只有49岁。
在热烈的会议间隙,几个赞比亚人时不时看向我,在场唯一一个中国人。
我知道原因,一款来自中国的发明即将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割包皮运动。
全世界割包皮的方法不止100种,工具五花八门,除了最原始的石头、树枝,还有刀、剪子、激光、电烙器,这款来自中国的工具是最快的――在过去,一个医生一天只能割掉20张包皮,依靠这项中国发明,未来,一天可以割掉100,甚至200张,真正实现流水化割包皮――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大概所有的赞比亚男人都将失去自己的包皮。
这不是通常意义上中国和非洲的故事:我们帮他们修铁路、修公路、建学校、建医院。如今,我们来帮他们割包皮。
前木匠的新发明
商环动画视频。来源 | 盖茨基金会
将中国与远在赞比亚的包皮连在一起的,是安徽芜湖的一场包皮手术。
2002年,芜湖大卖场老板商建忠因为反复的龟头炎,痒得受不了,躺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医生说,他们将用激光为他切掉包皮,这是最先进的手法――保证没那么疼。但结果他还是疼得死去活来,因为出血和伤口难以愈合,手术后又在病房躺了两个星期。
更加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他发现自己变短了,“最大化的时候,原来十五公分,现在十三点五。”
作为成功企业家,他曾经去到欧洲,在剑桥大学听闻了硬道理,“21世纪谁掌握了世界的领先技术,谁就掌握了财富大门的钥匙。”当时他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对于“创新”就觉得该当仁不让,没想到回来做了手术,虎落平阳,躺在病床上。他心绪难平,却有了想法:抚平和自己一样的男人们遭受的苦难,发明一款新的包皮环切器。全中国有7亿男性,就算只有百分之一来切包皮,那也是多大的市场!
这一年,商建忠47岁,大腹便便,他不只要二次创业,还要搞发明。年轻时,他在工厂做过木匠,算得上民科的水平,他买了一堆医学教材,一口气投入到发明的道路。凭着做木匠的经验,他决定运用哈夫原理,哈夫,就是英文“half”的意思,指的是将两个半环状物体连接成一个圆状的夹子,听起来有些高深,但建筑用的脚手架,就是靠这个哈夫夹来固定连接。哈夫结构可以锁死,非常牢靠,商建忠也要用这样的哈夫夹去锁死男人的包皮。
他设计了两个环,一个内环一个外环,分别固定在翻开的包皮上,先剪去多余包皮,然后通过内环和外环吻合,阻断包皮远端的血流,伤口自然皱缩凝血,学名叫“慢切割”。那场手术最大的痛苦,来源于出血和伤口缝合,他于是就要发明一种无须缝合、出血量还少的方法。
他想好了一个颇有些中产阶级趣味的口号,“让手术过程像喝一杯咖啡、吃一顿快餐一样简单。”
有了想法,就要做试验。商建忠找来一块七合板,将狗在上面绑成一个大字,用自己发明的内外环给狗割包皮。一开始当然是不成功,内外环不能无缝对接,阴茎上夹出一粒粒小肉芽,狗惨叫连连,邻居气得投诉,他又带着七合板和狗另找地方继续试验。一直试验到第九条狗,狗不再那么惨叫了,他离成功才近了一步。
商建忠将自己的发明取名“圣环”,原因言简意赅,“因为这是神圣的地方,又是圣诞的圣。”
女儿商晶晶说,这么取名有另一层原因,“我们家我们这一辈的小孩,家谱上都是圣字辈,父亲把它当作自己的小孩。包括我之前养的小狗就叫商圣欢”。当年,商建忠鼓捣发明的时候,商晶晶正在外地上大学,她后知后觉,只是发现自己的宠物狗不见了,好几年后,商建忠才告诉她,商圣欢是为科学献了身。
在动物身上做完试验,就轮到人体。每天都有陌生人来家里,商晶晶说,最让她无语的是,一块儿吃完晚饭,老爸就和陌生男人进了厕所,还关上了厕所门。
前七例人体试验都宣告失败,内外环套得太紧,血液不回流,志愿者阴茎血肿,苦不堪言,他每人赔了一万块。但商建忠不为所动,继续改进结构,除了对科学的执着,也因为财大气粗,“我当时有钱,我发财了,有几千万,赔得起,我一天就赚五六万。”
商环的发明者商建忠正在展示商环。摄影 | 盖茨基金会
2006年,圣环最终定型。商建忠甚至抵押了房产,但结果没人愿意相信他。当时圣环刚刚在医院使用,每一例手术,商建忠都跟去看。结果在那碰到了熟人,人家问他,你也来做手术?商建忠说,这是我发明的。人家一听就急了眼,你不就是原来在我家隔壁卖打火机的?这都能搞?那我不做了。
他想为自己的发明拉来投资,往返北京八十多趟,也没有一家公司愿意相信他这个医学门外汉。他还遇到了骗子,骗子告诉他,自己愿意投资一千万美元,但必须先在指定的公司做一份评估报告,他花了三万块做了评估,对方却消失了。
说起来因祸得福,正是在这份评估报告上,商建忠第一次知道WHO正昭告世界――割掉包皮可以降低艾滋感染风险。
“等于是骗子帮我们指明了方向。”直到如今,这份评估报告还被商建忠珍藏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2007年,得知比尔・盖茨要来中国参加博鳌论坛――这位前世界首富成立了基金会,正在全球致力于防治艾滋病。商建忠连夜请人将“圣环”的介绍翻译成英文,第二天就赶赴三亚,希望能见到首富,搏一次出头。
他差一点就成功了,“那天到11点25分,散会了,阿罗约和盖茨一起走出来,我就去递信,上面写了可以预防艾滋病的。但那封信没搞出去,盖茨走了,保镖把我拦住了。”
和世界首富失之交臂,商建忠只能带着他的发明,继续往返于投资公司、医院、各类男科医学研讨会,求着医学界的大佬们给一个机会做展示。2007年底,他来到一个男科大佬们的饭局,正要自我介绍,人家一听说他是推销“圣环”,就要把他轰出去。
美国康奈尔大学显微外科的李石华教授为商建忠解了围,让他留下,把发明拿给自己看一看。
“他拿了很多宣传资料,说自己是美国来的,因为我到美国去了这么久,一看这气质不像老美,但我当然也没好说。但是他这个技术,这种方法我在美国没有听说过。”李石华说,和这位民间发明家的初次会面,既不严肃还有些无厘头,但慢慢却有一点震撼。
他打电话给中国男科学会会长,“这将是中国男科学会这半个世纪以来,最有意义的一件成果。”
激动的比尔・盖茨
在卢萨卡,我旁观了一场圣环手术。手术室名称叫“theater room”。一个黑人小伙子走了进来,一手提着松垮的牛仔裤――手术前,护士已经在他的阴茎上涂抹了白色的麻醉药膏,他看了一眼我们这些诡异地站在一旁的中国人,眼神困惑。
“他们是中国来的医生。”打着领带的黑人手术师这么介绍我们,向他招了招手,让他躺好,把裤子褪下来。
他躺上手术台,两只脚板绷紧又放松,放松又绷紧。
“为了让麻醉更充分,”医生严肃地说,“我们要先按摩。”
他一边揉搓,一边再抹上些麻醉膏。身为男人,大概没有谁会不同意,如果麻醉不充分,这就是一场酷刑。
第一步是上环。医生拿出卷尺,测量阴茎的周长。圣环一共有24个规格,从A到Z,逐渐减小。这时出现了意外,黑人小伙子天赋异禀,一开始准备的环不够大。一般中国男人,最多使用到B,而在非洲,许多人要用到A。而黑人小伙子,要用到最大的A4。
黑人小伙子一脸无辜,医生摇摇头,示意手术暂停,他转向助手,“我们还有更大的环吗?”
幸运的是,库房还有唯一一个超大号,手术得以继续。助手用两把镊子夹住包皮,将包皮尽可能上提,形成一个四方形的包皮口。医生将内环从包皮口硬塞了进去。然后,翻转包皮,露出龟头,在内环的位置套上外环,嗒一声,内外环锁死。
小伙子全身僵硬,他倒是想抬头看看,医生一手将他按在手术台上,另一手塞给他一个手机,让他只管放轻松――虽然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
然后就是剪刀,沿着外环,咔嚓咔嚓,将翻出的包皮剪下一圈,动作干脆、精准,像在剪窗花。有猩红色的血渗了出来。助手熟练地用止血棉止了血。
“如果是过去的方法,出血比这个多太多。”医生不忘了告诉我们,由于内外环阻断了包皮末端的血流,这一点血不算什么。
五分钟,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手术就算结束。
医生微笑着看向一脸懵的我们,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多漂亮,不是吗?”
不来到撒哈拉以南非洲,不来到赞比亚,一个中国人很难对这场割包皮运动感同身受,这本质上是一场“自救运动”:手术免费,动员者挨家挨户动员,医生和护士不仅在医院,也在偏僻的乡村搭上简易帐篷,男人们排队躺好,手脚僵硬,场面经常血淋淋……官员们也不遗余力,赞比亚南部省的省长就亲身试刀,向媒体宣布自己割了包皮,他向其他男人喊话,如果他们还有疑虑,不妨回家问问妻子,“毕竟这是她们的玩具”。
2018年,商环手术在赞比亚的培训项目的一个试点社区医院,他们有专门的包皮环切科室。摄影 | 文艺
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医疗资源极度缺乏,14个国家中,乌干达只有13个泌尿科医生,肯尼亚只有100个护士,赞比亚也是半斤八两――2015年,14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12个没能完成预定的割除数量。
按照数据模型,如果不能百分之百完成目标,现有的割包皮运动一样不能遏制HIV在非洲的蔓延。撒哈拉以南非洲,急需一种手术简单、便于大规模培训的割包皮新方法。
商建忠的“圣环”就像是为非洲量身打造。首先,手术时间短,两个环一套上,剪掉多余包皮,基本就万事大吉,无须缝合,传统包皮手术要二三十分钟,圣环只需要3到5分钟,最快的记录诞生在中国,只用了40多秒。由于不须缝合,手术变得简单,不仅医生可以做,经过培训的护士也可以。
这成了这个故事最激动人心的一面:一个中国民间科学家的发明,可能决定着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至人类,与艾滋病战争的成败。
2009年到2012年间,李石华和他的团队在肯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分别进行了针对“圣环”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样本达到4000人――为了证明圣环可以大规模、安全地适用于非洲。这是中国产品在海外独立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临床评估项目――一共耗资1400万美金。
提供这样巨额资金支持的,正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创立者正是商建忠想结识而未果的前世界首富。李石华找到了基金会,向他们介绍了圣环。从美国总部到中国办公室,都决定试一试。
2012年,赞比亚的男性包皮环切中心诊所的工作人员向几名男子讲解和展示中国制造的商环的使用。摄影 | 盖茨基金会
2012年,临床研究结束,数据封存上交WHO审核。为了表彰商建忠的贡献,WHO将圣环改名为“商环”。
这一年3月,比尔・盖茨来到赞比亚,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亲眼看一场使用“商环”的包皮环切手术,二是他想带走几个商环。一个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演讲现场,比尔・盖茨掏出了一枚商环,将之作为中国“创新”改变世界的典范;又过了一个月,比尔・盖茨来到北京与商建忠见了面。
这成了芜湖商人商建忠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原本求而不得的世界首富主动走到了他面前,和他握手留念,“我们聊了40分钟,我说我愿意和他在一起,为艾滋病防治作出贡献。”商建忠激动万分,在比尔・盖茨身上感觉到属于伟人的气场,“他是真的伟人,世界巨富,永不下落的太阳”。
2015年,“商环”获得了WHO的预认证(PQ),这意味着作为医疗器械,“商环”通过了审核――这是中国医疗器械第一次拿到WHO预认证。
今年,在乌干达、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经过培训的本土医护人员将进行1000例商环手术,完成后,商环将有望进入各国政府采购名单。商建忠和基金会约定,将以成本价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售商环。
某种程度上,这也算为国争光。
4月,中国发明协会党委书记受邀出席美国国家发明家科学院年会,这是中国第一次被邀请,书记说了中国对世界的三个贡献,第一个袁隆平,第二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第三个就是商建忠。
发明家挺不住了
在赞比亚疾控中心的会议室,24个医生护士围成一圈,他们都有过用传统手术方法切除包皮的经验,如今被选拔来接受商环的使用培训。
给他们做培训的,是大个子的肯尼亚黑人Jairus。他站在最中间,接受被培训者的提问。
“手册说手术后七个星期不能有性生活?”一个黑人小伙举了手,一脸严肃,“这比传统手术要求的时间要长。”
“以你们的经验,他们能忍多久?”Jairus反问道。
会议室立刻七嘴八舌,有说一个月的,有说两个星期的,还有说他的手术对象就忍了四天。
“Crazy men.”Jairus耸了耸肩,大家都笑起来。
Jairus今年57岁,是一名男护士,他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被送往中国学习商环手术的第一个护士。Jairus出生在肯尼亚一个叫LUO的部落。他曾经有11个兄弟姐妹,其中6个都因为艾滋病去世。作为长子,他要养育死去的兄弟姐妹留下的孩子――一共12个小孩。这让他放弃了前往印度学习的机会,留在家乡成为了一名护士。
2009年夏天,他被选派到中国宁波学习商环的手术技巧。培训结束后,他也用商环做了一台包皮手术――中国病人看他是黑人,还不乐意――那台手术他只花了4分钟,现在他一天可以做100台。
Jairus见证了商环与来自以色列的竞争对手PP环的交锋。作为犹太国家,以色列全民都要行,对于包皮,他们远比中国人有经验。以色列人发明了一种叫PP环的环切器――商环还需要用手术剪剪去包皮,PP环却可以让被勒紧的包皮由于缺血坏死,自动脱落。
但以色列人的发明,后来却被证明不靠谱:没被切除的死包皮,到了第二天开始发臭,味道跟死耗子一样,装上PP环的人,没有人愿意跟他在一起。更致命的是,由于死包皮一直留在阴茎上,伤口容易感染。因为戴上PP环感染破伤风致死事件,在乌干达突然爆发了六七例。
“我们打败了他们。”Jairus语气骄傲,说的是“我们”。但他感到困惑的是,商环在非洲完全依赖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大规模临床试验后,基金会又投入了554万美金,用于进一步临床研究和帮助商环在非洲各国培训当地医护人员。
“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支持自己的东西?难道中国政府不知道商环是中国的发明吗?”
商建忠也是这么想的。他现在就想把中国政府拉进来,“现在在非洲给小孩子用商环做手术,他哪一天当总统了,他说我用的是商环,不是好事嘛。”
但有一个实际问题,要进入商务部援外的采购名单,按照规定,需要至少三家企业竞标,但商环目前仅此一家。
事实是,在与比尔・盖茨亲切会见之后,声名大振的商建忠日子并不好过。在国内,闻风而动的仿冒者让他苦不堪言,市场份额甚至缩小了。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一年利润只有200万,还基本来自政府补贴和税费奖励。非洲,也成了商建忠的救命稻草。
但他不懂英语,不了解非洲,面对非洲迟迟未结束的临床试验,只能干着急。曾经有人给他出主意,说自己可以帮他搞定非洲各国政府,他心急火燎花了钱,但这种在中国行之有效的方法,在非洲被证明是一场空。
为了满足WHO的要求,他扩大了生产规模,机器从2台增加到8台,员工从三四十涨到一百多。
“从2013年到现在,我就亏了三千万。”有时候,商建忠也会觉得被基金会放在了火堆上,“我知道,盖茨花了不少钱。搞了这么多年,把我们提到这么高的高度,但如果我挺不住了,拿货都拿不到。从感恩的角度要感谢基金会对商环的推广和帮助,感谢盖茨先生对全球艾滋病贫困地区的帮助,但我们现在挺不住了啊。”
上帝的计划
7月12日上午10点,我们和Erick走在卢萨卡的Chilenje市场,说是市场,其实更像中文意义上的街区,不过是有土黄色围墙那种。经过一个锈铁栅栏,就来到市场内部,一条条狭窄土路四通八达,两边是连片的低矮平房。
Erick说,这个市场属于一个特定的部落,在里面居住、经商的都是部落成员。每一条土路两旁,平房屋檐下都蹲着三两个部落男子,在工作日的早晨,依然显得无所事事。赞比亚失业率高达50%,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工作的劳累。我们还碰到了一个黑人青年,他很正式地和我们握手,说自己曾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但这并没影响他依然只能和同伴蹲在路边。
“我们到这里来,向他们介绍割包皮的好处,看一看他们是否愿意留下电话号码。”Erick今年27岁,是一个瘦高个的年轻人,留着山羊胡,他穿着一双锃亮的黑皮鞋,当Chilenje的土路把我们的鞋弄得灰头土脸,他会从兜里掏出手帕,将皮鞋擦干净。Erick属于这场割包皮运动最基层的一环――入室动员员,像他这样的动员员,在卢萨卡还有18个。
每碰到一个男人,他就上前问好,有时用英语,有时用当地的部落语。
“你切过包皮吗?”他首先这么问,然后他会说,“这是免费的。”
在Chilenje,我们遇到了一开始说自己已经切了包皮,但随后承认还没切的,因为他怕疼。还有人说“我不会改变上帝交给我的身体”,有人面对介绍不发一言,沉默以对,也有人主动来问,“我是HIV阳性,我需要去切包皮吗?”
这一次,Erick要向他们推荐商环,“这是来自中国的新技术,不用缝合,没有痛苦。”他信誓旦旦告诉每一个人。
但当只有我们的时候,他也会眨眨眼说出实话,“其实我也不了解商环,这是我接触商环的第二天,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无痛的,但我不可能和他们说这个一样很痛。我必须装作胸有成足。”
在市场的某些路段,满地都是啤酒瓶和威士忌的盖子,在Chilenje这个小小的市场,酒吧不下四五处,它们也是最热闹的地方。即使是上午,酒吧里也坐满了人,有年轻男人、中年男人、老年男人,有的人已经喝醉了。
“在我们这,四分之三的年轻人都喝酒。喝酒的时候,你感到开心,所有的问题都消失了,但一醒来,烦恼还是在那里,你只能继续喝酒。”
这是在一个经受贫穷和HIV病毒双重折磨的国家,最容易看到的自暴自弃。
“我不喝酒。”Erick摇了摇头。他成长在一个和Chilenje相似的街区,父母在他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他们的死因,“他们告诉我,我的妈妈是血液有毛病”。15岁开始独自生活,他曾经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司职后卫,但一次比赛他的膝盖摔碎了,“他们让我去一家意大利医院治疗,这需要3000科瓦查,但我没有钱。”3000科瓦查,也就是人民币2000块。后来他修过手机,在酒吧当过侍者,在药房卖过药,做过HIV的检测员,一年前他成了一名动员者。
他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不会永远当一名动员员。”他的语气充满乐观,他想存钱去读大学,学习公共卫生,“我想上帝对我有着计划,他不会毁了我的生活”。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过客,我想我明白Erick的意思,上帝对非洲也有着计划,不会毁了他们的生活。
就像Erick说,HIV并没那么可怕。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他从事HIV检测的时候,碰到了一对即将结婚的男女,女孩被检测出HIV阳性,男孩却没有。“后来他们结婚了。”
版权声明:本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归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撰文 | 张瑞 摄影 | 文艺 编辑 | 林珊珊 事实核查 | 刘洋 出品 | 谷雨 × 故事硬核
- 运营编辑 | 张琳悦 校对 | 阿犁 运营统筹 | 迦沐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