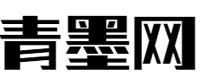他的星星和海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玩伴,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不以为意,等到分开时才发现他的重要。
读作者的文时,总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画面感。就好像那段略微泛黄的记忆呈现在眼前,闭上眼睛就能闻到海边扑面而来的咸腥气息,伸出手就能触到贝壳的纹络和颗粒感。
而很多人,往往分开了就不会再遇见,我们对于他们的记忆,便是命运最奢侈的馈赠。
终于我和樊星一样离开了家乡,我有很多与他的童年合照,照片里我笑得像朵向日葵,而樊星在另一边龇牙咧嘴,我很想念他。
2004年欧洲杯东道主葡萄牙队0-1不敌希腊与冠军失之交臂。黄金一代谢幕,菲戈和C罗一起抱头痛哭,谁也不知道那个眼眶和脸颊都红红的青涩男孩将来会是个巨星。我趴在樊星家的门缝儿跟他看完了那场比赛,而他躺在沙发上睡的很熟,转播结束之后电视机的屏幕散发着幽蓝色的光,蓝色的光映在没开灯的客厅影影绰绰,像是我想象中海的模样。
那一年我住在一个机关大院,院子很老很旧,但却是炙手可热的学区房,家长们争先恐后地把学龄的孩子送到这儿的老人手里,所以院子里除了上了年纪的老人就是半大的孩子。我和哥哥跟外婆住在一套小小的两居室里,那年的外婆头发已经花白,喜欢穿布料柔软的衣服,我哥比我大五岁,我会羡慕他脖子上的红领巾,喜欢他每天提着我的水壶带我上学。我哥已经爱上了金庸,我还不懂琼瑶。
大院像是一个巨大的广场,住在里面的人们千姿百态,热闹非凡。院子铁门上的红色五角星已经逐渐在时光里氧化,我得仰着头才能看清它旁边钨丝灯的样子。老人醒的比我们这些孩子都要早一些,清晨天蒙蒙亮,每当我还得靠揉揉眼睛来提起精神的时候都得花好几分钟来回忆如何称呼公共盥洗室遇到的奶奶和婆婆。我笃定地相信人与人交往的方式很简单,就像是我跟大院里的婆婆们问好,就一定会得到回应;放学跟同龄人在长长的走廊追逐的时候,随便推开一扇门就是个可以歇脚的地方;墙根的野草每年春天都会在约定的地方长出新芽;就像是,缓慢踱步的时间把年老的他们跟我们一同归为孩童,与激烈争斗的大人世界隔离开来。
而至于那时候樊星,他绝对是我非黑即白的世界里的灰色地带。
比如,三年级,我是班里第一个加入少先队的同学,语文老师让我站在讲台高声朗读我的第一篇作文,我是班里的行为标兵。但是在班长竞选中我输给了樊星。我对他的演讲嗤之以鼻,他没说要带领班级在运动会上得第一,也没说要让班级成为卫生免检,而是拿着小塑料瓶装着指甲盖大小好看的贝壳分给全班三十多个同学,他骄傲地说他爸爸是潜水员,这些贝壳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底。
在我眼里,这是不折不扣的贿赂。但是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那个被我攥在手心里的塑料瓶子成了我心里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在提醒我,一个成绩不如我的男生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而他住在我隔壁。
樊星的成绩是班里的千年老二。当然,是倒数第二,我常常拿着那个装贝壳的塑料瓶砸他的脑袋,偷偷拉开他的书包,站在大院的广场上把那些布满红色叉叉的作业本抛向空中,看着作业本在空中变换着姿势绽放出不同形状的花儿来,我不知道那时候他脸上的红色是恼羞成怒还是落日的余晖落在他的两颊。我像是整个院子里的小霸王,而褪去班长威严的樊星是个受气包。外婆会拿着一个傻瓜相机对着我俩乱拍一气,我喜欢每一次闪光灯亮起的时刻,我喜欢冲着镜头笑,然后用胳膊搂着樊星的肩膀,把他的脑袋摆正。那些照片里的我们永远年轻,哪怕它们是跑焦了,漏光了。
时间的流逝往往和人类之间的离别不成正比,也与人类成长及衰老的方式不同。随着时间流逝,我们成了大院里不断快进的电影镜头,而外婆他们成了电影沉默而温柔的背景,像是挂在墙上那个古老钟表的重锤,缓慢地,记录着每一个时刻。
樊星似乎把所有属于男孩子旺盛的精力都献给了奔跑,因此在他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很难轻而易举的抓住他了,他像是旧日穿堂而过的风,外婆棉布衣服柔软的下摆在那风中摇摆。
他像是没有蝉鸣的夏天,没有云彩的落日,让我带着一点遗憾去喜欢。后来早晚洗脸的时候在公共盥洗室看到他拿着白色双喜搪瓷盆练习憋气的时候,我都会绕到他背后猛地按一下他的脑袋,他抬起头的时候前额的碎头发湿漉漉地黏在一起,脸颊很红也很狼狈,我依然会开怀大笑,像是攻下了一座山头。
樊星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高中之后路过他家门口的时候还是会透过门缝看看那间小小的房子里在发生着什么,长高了的樊星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躺在沙发上睡着,再也没见他看过球赛,倒是发现他渐渐沉迷收集好看的贝壳与潜水工具。我会很期待每天与樊星的相遇,期待着天空泛起鱼肚白,闹钟铃声响起的时候,我张开眼睛恰好看到晨跑的樊星路过我卧室的窗前。期待着看到樊星很差的成绩单,会让我以嘲笑的方式与他产生交集。时间像是季风带来的洋流,推着我们一直一直向前。
此时的大院附近已经高楼林立,在大院疯狂生长的爬墙虎叶子的间隙露出的斑驳墙壁与周围的混凝土与反光玻璃格格不入,城市像个长着大口会吞噬我们的怪物,而我们生活在孤岛。
高二暑假的一天,我在一座立交桥的桥洞下发现了樊星。樊星的精神似乎很好,平整的白色T恤上印着一条蓝鲸,很好看。
我在樊星身边坐下,这是我跟樊星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和平年代,或许是因为我最终还是读懂了琼瑶。我低头看着樊星修剪整齐的指甲说,樊星你给我讲个故事吧,你要把我当朋友。他看着我,眼睛睁大然后又合上。
十七岁以前,樊星的梦想是像他爸爸一样做个潜水员。
他收集着爸爸用旧的潜水镜,脚蹼和他从深海里给他带回来的贝壳。他像是生活在一个冗长的梦里,在深蓝色的海洋里,在未知的世界里。他会像个第一次接触游泳的孩子一样在脸盆里练习憋气,在浴缸里浸泡很久,在冬天鲜有人去的海边畅快呼吸然后悄悄游进深水区,他试着伸手去抓住海底那些我们未知的东西,但总感觉自己的未知在膨胀。
樊星的爸爸去过很多地方的海,他经常远行,很久才会回来。而他最后一次出发是在一个肃杀的冬日,樊星甚至没有和他告别,樊星并不知道他要去的是哪片海,多久才会回来,仿佛是可以重复无数次的电影镜头,因此没有看到他满是胡渣的脸庞上扬起的温和笑意也会在下一章节补充回放。
樊星记忆里的爸爸是一个温的人,像是被阳光温暖了的海水。他是樊星第一个崇拜的人,或许也是最后一个。
打那次起,我和他成了真正的朋友,樊星生日那天,我们去电影院的包间点了一部1982年的旧电影,名字叫作《碧海蓝天》。
Jack在海边把一个故事娓娓道来,他的眉眼一片虔诚而温柔。
“你知道怎么才能见到美人鱼吗?下到海底。在那里海水甚至已经不是蓝色。蓝色也仅仅成为回忆。正在寂静中你漂浮其中,呆着。要下定决心为他们而死。只有这样她们才会出来见你,判断你对她们的爱有多深。如果,爱为真,爱为纯。她们就会和你在一起,带你永远离去。”
结束的时候,樊星问我,海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我说,爱你的人是不会离开你的。
樊星轻轻的点头算是附和。可我知道“你属于大海”的含义,樊星的偏执属于那里。
在很多天之后,十八岁的樊星跟我以及十七岁的樊星告别,他的告别像是在宣布一个结果,不带过程和任何铺垫,像是夏天突如其来的大雨,我来不及去运算,去组织语言,然后就要和他说再见。
樊星离开的毫无征兆,却又顺理成章,就像是我在他离开的那一年,偶然间看到的一场欧冠比赛中C罗在足球场上脚尖奔跑,我看到了礼花与欢呼起来的人群,他握起拳头的样子已经和2004年那个稚嫩的他完全不同,所以,我知道,樊星也终于变成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自己。
外婆步履已经蹒跚,每周她都会带我到樊星住的小屋扫扫灰尘,当钥匙插进生锈的锁孔,仿佛是打开了回忆的闸门,我很想念他。
他带走了贝壳,带走了关于那些梦里的回忆。屋子里那瓶海风香薰还剩下半瓶,用了大半管的牙膏依然是按照之前那样摆放着,阳台的花儿开的正是最好的时候。旧旧的脚蹼和开胶的红色帆布鞋被樊星放在显眼的位置,在提醒我,在回忆他。
又是一个夏天,我跟外婆一起坐在大院的树荫下,看着迟暮余晖的灿烂洒在外婆的脸颊,深深的皱纹和白色的头发上,外婆的蒲扇摇得很缓慢,不知道是谁家的钟敲了整整六下,此时我已经可以耐下性子听完三十秒的钟声,外婆的相机放在家里不起眼的位置,跟我同龄的孩子们不知道去了哪儿,但是我知道我也会离开的。
我跟外婆走的很缓慢,大院也变成了一个通往未来的慢镜头,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所以我想让所有的过去和现在都走的慢一点。
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樊星去了哪里,或许是在被麦田染绿的梦里,或许是在被风筝带上蓝天的梦里,或许是在被海洋拥抱着的梦里,或许是被在海豚亲吻的梦里。
那么亲爱的樊星,你是否到达了你的世界?
凉茶-,活泼可爱的处女座,沉默寡言的艺术生。制造一个时光机,永远活在青春里。微博:@陛上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