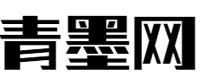好多年前,每年春节回老家过年,爸总会买一桶红星二锅头。那种10斤装的大桶,拎着上客车下客车,到了一个小城镇还要倒一次车,但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因为那酒是带给大伯的。
小时候,不晓得大伯比父亲大几岁。看上去要大很多,他们的面貌倒是有几分相似,气质却有天壤之别:父亲是武装部的干部,衣着得体,气宇轩昂;而大伯,在我的记忆中,冬天永远是那身灰扑扑的旧棉祆,面容也是黝黑的,额头早早就有了深深的皱纹。但是多年以后,我才醒悟其实那时父亲和大伯都还年轻,也不过三十多岁,大伯其实只是比父亲大了两岁多,是农村劳苦的生活,让他早早就苍老了。
他吃饭的时候会喝点儿酒,很陶醉于爸带回去的高度二锅头,说这样的味道才像酒。那种高度酒,平常父亲是不喝的,但每次和大伯一起,他会喝上两杯,至微醉。
在我印象里,他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有少少的对话,关于村里的人和事。大伯话少,说话又慢,常常是父亲问起来,他答两句。若父亲不开口,两人便沉默,沉默地对饮着。
有时我会疑惑大伯和父亲的感情,明明是亲兄弟嘛,交往却那么少,也不觉得有多亲。在我记忆中很多年,大伯却从不曾去过我们家。也不过是200公里的路程。我曾经问过父亲,父亲想了想说,大伯不爱出门,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老家的县城了。
我不是太能理解这种生存空间的窄小,但之后也没有再问过,只是再回老家,我已经晓得替父亲去给大伯买二锅头,一定要大桶装的。
大学毕业工作后。大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不能再喝酒了。那以后,回老家的包裹中,再也没有了二锅头,而是换成大包大包的药物。父亲每次都是自己拿了医保卡去大药房把药买齐,然后戴着老花镜把服用方法写在一张纸上,字写得很大,回去后,会叮嘱堂哥好多次,按时给大伯服药。
他们都老了。在一起,话依然是少少的,少少的话语中,翻来覆去也只是重复的叮嘱,好好吃饭、按时吃药、有事打电话。但大伯,从来没有主动给父亲打过电话。母亲常感慨,大伯是天底下最省事的农村亲戚了。有一年回老家时,父亲跟大伯发了脾气,因为我唯一的堂姐出嫁,大伯竟然没有给父亲说。
父亲生了气。大伯的言语还是缓缓的,他说:你们回来也是花钱,在外面赚钱哪有那么容易?刮风下雨的都得去上班,还得看人脸色。平常买米买面的都要自己花钱,房子又贵。不比我们,自己地里都有,连油都是自己打的,天不好就在家睡觉,老天爷都管不着农村人,比你们活得容易。
我愕然。那是我第一次听大伯说那么多的话,忽然觉得那么多年对大伯和他们那种生活的同情有些苍白。连父亲都不知该说什么,嗫嚅片刻嘀咕一句,不管怎么都该说一声的。
没想到是生活中一直养尊处优的父亲,身体先出了大问题。常规体检中查出了食道癌,在省城医院做了手术。父亲手术后回到家,才告诉了大伯。于是,大伯第一次去了我们家,带着全家人,租了一辆面包车。车里塞满了成袋的大米、白面及花生油、土鸡蛋,甚至堂哥自家大棚里的黄瓜茄子。
因手术后进食困难,父亲瘦得厉害,堂哥进门后,看到父亲,背过身去便落了泪。唯有大伯很平静,拿了凳子在父亲对面坐下,问父亲:吃不下东西?
我跟大伯解释这种手术的弊端,会在很长时间里影响进食。大伯没有听完,便摇头打断我,对父亲说:别听医生说的那些,只管吃,只要能吃饭,什么病都不怕。你就只管吃饭,不吃药也没事。
疾病的折磨让父亲极其憔悴,但大伯的初次登门,还是让他很激动,用力点头。
但是一年后,癌细胞转移到淋巴,父亲再次入院,且情况非常糟糕。大伯急匆匆赶去医院的那天上午,父亲已经进入昏迷状态,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无法探视。
大伯在封闭的监护室的门外愣愣站了许久,不管我们如何劝导,他不离开,也不说话,直到夜晚,才被堂哥硬拉走了。
两天后,父亲去世。按照父亲的遗愿,我把他带回了老家。
守灵的那晚,大伯拿了一把凳子坐在父亲棺木旁,不说话,就那么坐着。隔一会儿站起身来握一握父亲的手,看父亲手中的小元宝是否握得牢固;又整理一下父亲的衣服,看每一粒扣子是否扣好一遍遍检查过,才会坐上一小会儿。隔上几分钟,又会站起身来。
长明灯幽幽地亮着,浅浅的灯火里,大伯的神情是平静的,看不出任何痛苦,也没有一滴眼泪。只是这个80岁的老人,面容越发显得苍老和憔悴。
父亲一周年祭日的时候,回老家给父亲上坟,大伯用手拔着几棵春天里长起的荒草。坟土拢得很齐整。大伯的两只羊,就在不远的草坡上悠闲地吃草。大伯慢慢摆上祭品,大伯什么食物都没有碰,只是倒了两杯酒。
弯下苍老的身躯慢慢倾洒在碑前。我的鼻子一酸。大伯忽然直起身来问我,那时候,你干吗非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去,不让见最后一面?
我一愣,半天才意识到他说的是重症监护室。过了那么久,他还记着。那到底是什么破地方?他唤了一声我的小名,他说,你当时怎么想的,把他送到那里去?
我当时当时只想做最后的努力,能留住父亲的生命,哪里想得了那么多。可是,我要如何对他说?他是如此计较,始终耿耿于怀。
大伯我,他摆摆手,不再看我,自语道:都不在他身边,他一个人多害怕呀。然后我看到有混浊的眼泪,在他眼中缓缓流出,沿着他面容间遍布的皱纹纵横。
在父亲离开半年后,他哭了。而他的眼泪并不是因为父亲的离开,到了他这个年纪,用他的话说,生死的事,早就看开了。让他疼痛的,只是最后一刻,他不能陪在父亲的身边。
为此,他怨我,不能释怀。我的心再一次疼起来,想起父亲手术后在病房,说起的那件久远往事。
当年,父亲和大伯一起报名应征入伍,大伯的条件更好一些,被接兵的首长一眼看中,两个人都可以走。奶奶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仅有的两个儿子同时离开,痛哭不已。后来大伯对父亲说:你走。说完大伯就没了踪影,一直到父亲走的时候,才不知从哪里跑回来,又对父亲说:走吧,家里有我。前前后后八个字,定了结局。
就这样,父亲走了,大伯留下来,两个人的命运从此天差地别。大伯从不曾有任何遗憾和抱怨,甘心任命地沉淀在这样一种命运里,默默地,静静地。一如当年,他的担当和父亲的接受,那么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或许大伯知道,若他委屈抱怨,父亲在外面必不能活得心安。也或者,对他们的感情而言,原本,就没有谁付出谁亏欠这一说。这就是他们的感情吧,有生之年,他们相处的时间有限,更没有过什么关于情感的对白和承诺,只是一对寻常的兄弟,小事不扰,大爱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