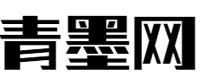我已经很久不看当下的文学作品了。
一个专业的文学从业者,都不看作品,是哪里出了问题?
作家通常会把问题归于时代,他们认为:
这个时代被网络分割的越来越碎,留给文学的时间越来越少,如今连碎片都被抖音、知乎占据。哪里有时间阅读文学?
这个时代的生活越来越千篇一律、机械复制,可供挖掘的诗意也随着乡村崩溃而消失,城市生活一地鸡零狗碎,写无可写。
这个时代的人心浮躁,年轻读者在鸡汤文学中成长,中年人被成功学所蛊惑,无暇顾及文学,老年人知识结构腐朽,不是目标读者。
这个时代对文学越来越不友善,各种消费主义挤占了文学市场,作家生存环境堪忧,稿费低,税率高,出版社不出中短篇小说,生活得不到保障。
总之,都是时代的错。
但是否有人从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看一篇小说?
阅读小说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
事实上,读者对已经定型已成惯例的作家们的文学操作感到深深地厌倦。
业余写作者独眼老师曾在连续阅读了十几天国内作者写的小说后总结道:
“ 男作者写的是:农村、废旧的工业区、三线以外的小城、城乡结合部;男主人公的童年-少年-青春期,跳到颓废中年;总要写对女孩胸部的意淫、对手淫的迷恋和恐惧;浑浑噩噩的性,不明不白的爱;有些描述真假莫辨,可能是吹牛也可能是想象;
所有父亲都打儿子,三分之二父亲还打老婆甚至自己的老子,一半早死,另外一半老了之后都怕儿子,母亲都活得比较长;母亲可能温柔懦弱也可能暴烈,但永远是别人的妻子或母亲话更多;故事更像传奇,好像有点儿什么意思,又可能也没什么意思,有可能是装腔作势,也有可能那种没什么的无力才是装腔作势。如果不靠方言,短促、平白假装口语的语言夹着一些四字成语,又很统一,他们的小说像一个人写的。
女作者写的是:大城市(多数北上杭)、外国;女主人公的青春期,多数高中至中老年;所有围绕爱情和家庭的计策、算计,没有一个笑容、没有一句话是无意义的;父亲多数软弱,母亲啰嗦、强势或者推卸责任,其他家庭成员琐碎、给人施加压力,隔代人往往神秘体贴;无论这些故事在写什么人什么事,那背后一定有一个教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她们在试图把道理讲透,所有的材料都是为了讲至少一个理,而这个理绝对不能白讲。语言带着一点儿翻译腔,一些台湾腔,一些上海腔,不像一个人,每篇小说都像一群人在说话。 ”
这条微博收获了3000个转发,1110个评论,3400个赞。在为数不多的文学爱好者里,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赞同。
独眼老师总结的还是写什么,我可以再针对我所熟悉的青年作家群体,说说怎么写。
首先,他们写人,不写人物。有些小说就一个主人公,满篇自怨自艾。有些小说,登场的人不少,都是为了衬托主人公而存在,主人公则是写作者的观念叠加。年轻写作者,在写人时太过屈从于时代打在人身上的外部痕迹,可以毕肖,但总是被生活推着走,没有自主意识。而塑造“人物”必须专注于深邃,处理人物性格的复杂层面与厚度,这考验作家的思想能力。
人物要靠什么来塑造?详实的外貌细节,深邃的性格,特质不会自己浮出水面,要靠复杂纠葛的人物关系,以及处在不同关系中的应对方式来呈现。新时代出现了新型人际关系,但当下文学作品鲜有涉及。 没有丰富的他人世界,只有单调、重复的自我认知。人往深里走,却不往宽里走,活在安全范围和作家的臆想世界里,不与现实发生碰撞。
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如何不涉及关系?除非这是个不健全的人,比如身体残缺者、精神障碍者,性格偏执者。 所以当下文学作品涌现大量有缺陷的人,作家仿佛不会写一个正常人。 有缺陷的人和人的缺陷是两种不同的写法,前者是夸大缺陷,造成人物性格的扭曲,以此挣脱社会关系的束缚。后者则是描摹缺陷的合理性,和对缺陷的有限修复。
作家要么回避对于关系的处理,要么就把关系写得拧巴,比如父母伤害造成童年的阴影,家族记忆埋下刻苦的仇恨,相爱相杀。反观一些职场、官场小说,恰是因为处理了人在关系里的纠缠,铺陈了每一段关系选择的合理性,而受到欢迎。尤其是历史背景小说,人与人间关系的微妙,可能会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
为什么不写人物关系? 因为年轻写作者深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擅于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且坚信自己是独立的个体,现实世界的“局外人”,总是以一副冷眼旁观的姿态审视一切。
但中国正在被新型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式所重新结构,在结构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在被重新定义,提倡的是一种全民参与感。看起来被切割成原子化的个体,重又勾连起一条新的线索,生成新的人物关系,比如主播和打赏者,拼多多组团,粉丝团里分工协作。 新的人物关系,其实质是新的经济关系与道德认同的确立。而如果想准确把握这些,既需要写作者敏锐感知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的变化,又需要一种宏观的对于这种革命性变动的理解力、阐释力,这就涉及中国作家知识结构的更新。
写作者并非对新式人物关系熟视无睹,但却无法把握背后所蕴含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变动,只能在公共平台表现出一种慌张感,说些不知所云的抱怨,仍沿用既定的方式看待问题,在文学作品里高唱挽歌。 写作和现实间出现了巨大的错位。本该属于文学的位置让渡给了深度报道,因为报道最重要的事情恰是给出背景和厘清关系。
如果不写人物关系,那怎么写人物?年轻作家想出了办法——写细节。年轻人对于细节的敏感度远胜于前辈作家。女作家会不厌其烦地写一件衣服的质地,男作家会努力回忆第一次触摸到异性肉体时细枝末节的感受。
一时间小说里充满了大量的细节,如何在细节的海洋里脱颖而出?不是靠有效性,而是靠写别人没写过的细节。有些细节,只限于某个职业,比如警察、麻醉师。有些细节独属于某一阶层,比如中产阶级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在世纪之交的小资写作风潮特别受到追捧。那时读者从安妮宝贝作品里的细节按图索骥,装扮生活,也树立起了虚假的自我意识。
“ 崔全松坐上飞机,便将熊本熊眼罩妥帖佩戴,欲小憩。去年他去日本出差一周,未听王泽月临行忠告,仍是任性带回一行李箱日本设计中国制造的小玩意儿——真的都只是些小玩意儿。比如一个撅起大屁股的比基尼玩偶,可以在泡面时用臀部帮你压住杯面纸盖;比如豆腐切丝器,事实上夫妻两人从来既不吃泡面也不吃豆腐,两人同时对豆制品过敏;再比如压力发泄球,特殊塑料制,耐摔不会破,只是砸地板上会变得非常像黄绿色鼻涕;黏在玻璃上也不掉落的橡皮超人,紧身内裤外穿,没有披风,臀部比泡面更显眼。还有一对可以放在车顶做装饰的兔子耳朵。王泽月并不认为他们那辆黑色凯迪拉克旗舰商务版三厢轿车适合这对粉红色耳朵和纯白的小圆尾巴……如是,这些小东西从中国漂洋过海到日本售卖、从日本漂洋过海抵达这个中等偏上北京家庭,此后,其命运轨迹便已注定一无是处,不过是从储物间走向垃圾箱。
包括这幅眼罩,但也不包括这幅眼罩,因为它眼下貌似派上用场,正在发挥价值。崔全松果真相信熊本熊卡通眼罩足够体现他的品味么?眼罩纯棉、全黑,熊本熊的两只小圆耳朵支在眼罩上方,替佩戴者遮挡眉毛。这只名为熊本的虚构之熊,尊荣大致如此:面黑、眉白,眼白敞阔,眼白内不怎么严肃地印上两个黑点,权当眼珠。崔全松的微信里装有几套熊本熊的表情包。所有表情图里,熊本熊都大张熊嘴,并不见一颗熊牙。 ”
这是一位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作品,全文充满了琐屑的日常生活细节。她所提及的日本设计、熊本眼罩都属于特定的中产阶层,即便琐屑,也努力彰显着中产阶级的生活趣味。我们赞叹作者对物质细节敏锐观察的同时,也好奇这种琐碎的细节罗列,对于阅读有何意义?
能否给读者一个阅读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中产阶级夫妻在机场喝咖啡,吃沙拉的故事?为什么要去阅读眼罩品牌,豆制品过敏的细节?或许这些细节于作者是精心发现,细致打磨的,某个细节可能触及到她的灵魂。但于广大读者,既没有借鉴意义,也无分享意义,更不会产生共鸣,带来思考。
我们阅读着别人的生活,与己无关。
这种细节的堆砌,造成了小说篇幅无节制的膨胀,在中国,中篇小说比短篇小说更受到重视。由此,小说家拼命地填充细节,用成百上千字描摹无关紧要的情境,喋喋不休描写物质,只为了让虚弱的小说迅速膨胀起来,由此患上了一种细节肥大症。
这种细节写作法,有80年代文学传统和欧美文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更多的是一种风格学意义上的。 更多是来源于人物悬空症,即,作者不再处理人物赖以存活的生活关系,人物被写作者从它们的生存基础上连根拔起。
好的写作,是试图回应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即便无法把握整体,也可以从一个小切口突破,重新去关照被遮蔽的现实。是由写作者的触点,连接到了读者的生活,引发共鸣。是被有效细节激发出对世界全新的感受力。
大部分写作,尽管文笔不错,讲究技巧,也有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但一是仍处于已知传统知识范畴和经验范畴,难以超脱。写乡村、写小镇、写城市都有固定的套路。塑造的人物也不外乎自恋的小镇青年,做噩梦的北漂沪漂,爱上摇滚乐手的文艺女,性冷淡的中产夫妻,每个人都被贴上了一个鲜明、粗暴的标签。二是将观察力误认为是洞察力。观察是基于表象的看,好的写作者加以提炼,一般的写作者忠实记录,不称职的写作者片面呈现。而洞察力,是穿透表面深入本质,是建立在对世界的全方位认知基础上的新发现。
人都有对于未知的着迷与渴望,所以读者会选择抖音、知乎、微信公号,这些能提供给他们新的认知角度的媒介,而放弃文学。
非虚构写作的成功应该让中国的虚构文学创作者警醒起来。他们多是一群业余写作者,但文字迸发出一种久违的生命力和活力。他们讲述的故事既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故事里带出的细节又对人性一击即中。他们重新去构建、展现人物关系的多重可能。至于非虚构写作如何定位或提升自己的文学性,同样是极为重要的课题。
近日,鲁迅文学奖十强入围名单出炉,有朋友推荐了篇叫《良霞》的小说,读毕,我对作者处理主人公良霞的手法很感兴趣,设想如果换成其他作家,会如何处理一个美好少女的远大前程突然被罹患疾病所改变。
我大胆揣测了一下:新锐小说家弋舟先生会让人物扭曲纠结,深挖内心世界。非虚构写作者梁鸿老师会让人物辛苦坚忍,同时把外部环境渲染得一片糟糕。阎连科老师会找一个有权利的男人把良霞玷污掉,全村疯魔。张悦然女士会写嫂子照顾良霞时微妙的女性情谊——这就是写作者世界观的选择。
平心而论,当下的文学创作环境已经有了不错的改善。较为完善地形成了写作、发表、评论、奖励的一条龙机制。一部好的作品,应该可以获得不错的受益,以及专业人士的重视和来自不同部门的褒奖。同时,文学和商业的紧密衔接,又使得文学作品被资本市场所瞩目。影视改编、付费阅读、商业讲座,都提供了作品后续开发的可能。至于作家所抱怨的读者越来越少,我觉得并非如此。电子阅读器、微信公号、非虚构写作,重新拉回了文学读者,只不过他们阅读的平台、品牌有所改变,一些作家也尝试向着新媒体平台转型。
并非读者不爱阅读了,而是虚构的力量越来越孱弱。读者的阅读习惯已经无法忍受细节的堆砌,和凄苦哀愁的心理独白。 作家应该寻找到一套新的表述方式,这必然对写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否有一颗宽忍之心,是否拥有一个容纳人性复杂性与世界宽广度的精神世界,让文学在其中谦逊平和地学习成长进而游刃有余。 写作者还必须时刻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从各种渠道寻找资源,单以文学构建世界观,尤其只从现代主义寻找精神资源的人,是不完整的。
有人说: 文学要想重新挽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尊严和读者,是需要在准确认知现实的基础上,重新提供矫正现实的视角,这一点,非虚构和深度报道反而走在了中国文学的前面。 眼下中国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结构断裂和价值转型,它给文学提供了更广泛的素材,需要写作者的宏观视野和微观聚焦相结合。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文学里重新了解中国。
【注】本文内文配图均源自视觉中国